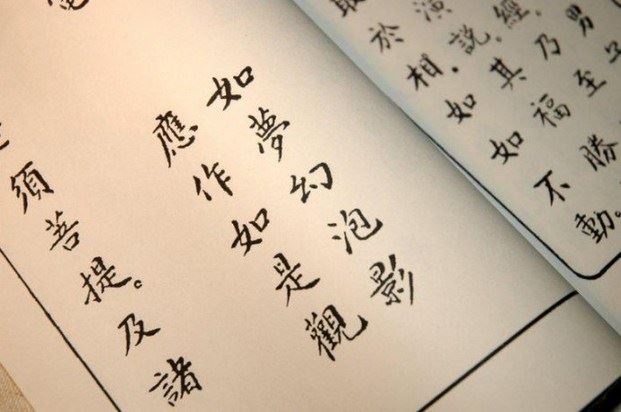肥西县是安徽“第一县”,桃花镇则做了多年的“安徽第一镇”,而我要说的“桃花城”就是现在的“桃花镇”。
合肥地区用“桃花”来做地名的很多:合肥老城北原有个“桃花村”,现在成了“桃花社区”;肥西县三河古镇有个“桃花岛”,是景区的一大组成部分;三河镇西边,肥西和舒城交界处还有个“桃溪镇”……
这说明,合肥地区不仅桃树常见、桃花常开,而且民众喜欢“桃花”。也难怪,桃花不仅花开艳丽,而且它还是最早报春的花卉之一——“竹外桃花三两枝,春江水暖鸭先知”嘛——还有一点大家不要忽略了,贫穷时代的农村,桃呀、梨呀、石榴呀,这些才是农家孩子吃得到的水果!
肥西的“桃花镇”,早先是“二十里埠乡”,后来又改名“肥光公社”、“桃花乡”,因江淮汽车主要在此成为肥西的主要税源地,上世纪90年代建“合肥经开区”时,肥西舍不得把它全部交出,就像挤牙膏一样留下了沿合安公路的一条狭长地带,设了个“桃花镇”,只是把个经开区“一分为二”了。而正是这一“留”,让肥西经济“桃花处处开”,成了“合肥第一县”,进而“安徽第一县”!
“桃花城”其实没“城”,只是民众口中的“城”。这个“城”来源于一个传说。据传大约是在宋代,有个放鸭人要回去吃饭,就随手将桃枝做的赶鸭杆插在了地上,等他回来时,赶鸭杆已变成一棵盛开着桃花的树了。而且奇特的是,十个枝头中,有九个是绽满了鲜艳的花朵,只有一枝没花。有老人就说,这一枝不开则已,开了就会有好运。所以当地有民谣:“十枝桃丫九枝开,一枝单等状元来。”有些人为了讨得吉祥,就想在此建“城”,于是就有了“桃花城”之名。别以为是我胡扯,这是多个方志典籍里记载的,比如《肥西县地名录》在“桃花城”下有附记,《舆地纪胜》卷45《庐州》也有桃花城“在合肥县南四十里”的记载。
除了“桃花城”,还有“三官殿”。所以,“桃花城”虽没“城”,但在民众心里却自古以来都是“宝地”。的确,在这块“宝地”上,就诞生了一个赓续数百年且饮誉四方的名门望族——龚氏家族。庐州曾有一首民谣:“一世、二世,孤苦伶仃;三世、四世,渐有书生;五世出一高僧;六世车马盈门……十三、十四,两代翰林。”可见龚氏一族的精彩。而这个家族最出名的一个当属龚鼎孳了。
按清嘉庆的《合肥县志·古迹分志》记载:“国朝赠兵部尚书龚孚肃墓,在城南桃花城……国朝礼部尚书龚鼎孳墓,在巢湖庵后,赐祭葬。”龚孚肃是龚鼎孳的父亲,其墓是明确在“桃花城”的;但龚鼎孳墓所在的“巢湖庵”在哪里呢?近年来文物管理所部门多方调查,未有定论,有说在桃花镇的,有说在巢湖中庙的,但有一点,龚家是桃花城人没有异议的。
现在的合肥人,知道龚鼎孳的估计不太多,但在从前,龚鼎孳却是大名鼎鼎。这是一个集“神童”“才子”“情种”“杠头”于一身的人物,又是一个在“忠”“奸”上饱受褒贬的一个人物!
据说他“生而歧嶷,颖慧夙成”,少年时代文名就冠绝同辈,且博通骚史,是当时有名的“神童”。他18岁就考中进士,19岁被崇祯帝钦点为湖北蕲春知县,不久因抵御张献忠军之功,24岁升任兵科给事中。他不仅“官运”亨通,且“桃花运”也旺,赴京途经金陵时“冶游”认识了“秦淮八艳”之一的顾横波,一见钟情,三顾“迷楼”,一掷千金,如愿“抱得美人归”。“迷楼”是顾横波在秦淮河畔的住处,本名“眉楼”。龚鼎孳亦是忠实的“迷粉”。
在中国文化里,“桃花运”是个很有意思的词,是用来指男女在爱情方面的运气,按命理又分“墙内桃花”和“墙外桃花”。龚、顾的爱情应该是“墙外桃花”。据说“墙外桃花”的人性格开朗,有气质和魅力,多潇洒美丽,喜欢浪漫激情,且人缘好,擅长处事交际。龚第一次见顾时,顾并没有特别中意他。但痴情加才情,终于打动了被“众星拱月”的她,成就了一生的彼此相守。
龚鼎孳曾曾写过一组《点绛唇》,其第四首《罗敷媚》是这样写的:“前身定解星前语,生就玲珑。多谢东风。放出桃花满镜红。分明六曲屏山路,那得朦胧。心似孤蓬。长系残香薄醉中。”对着以“画兰”闻名的心爱,他“多谢东风”给他送来了“桃花运”。而且,他的爱是来真的,相比于同为“八艳”的其他姐妹,顾的命运算是最好的一个——年貌相当,温柔多金,前程似锦,如胶似漆!龚鼎孳写给她的无数收在自传性传奇《白门柳》里的热烈的情诗,今天读来,仍见到一片浓郁到化不开的深深爱意!
而在他的家乡桃花城,他的“墙内桃花”——妻子童夫人为他坚守着,却又不干预他的恣意纵情。“彩旗飘飘”时能“红旗不倒”,可能是夫妻真的恩爱,也可能是真的“看开”。我想到了一个人——胡适。
他的这种“好运”在他28岁时出现了波折。那年李自成攻陷北京,龚鼎孳投井被救,出城又被阻,“迷”了心眼的龚鼎孳被迫先后接受了大顺和满清的授官。虽然他后来又“官运”仍算“亨通”,做到了尚书之职,但因其政治上的“一臣侍三主”,被正统思想归为“贰臣”,饱受到讥讽。他以“杠头”的面貌冷眼对待政敌,可能是源于性格,或许也有借此“掩饰”的成分。
他在自己的作品中,无限追忆少年时的意气风发,也深深感慨时代播迁的宦海沉浮。他的《诗集》中,花愁泪痕、寒雪孤鸿、疏灯萧瑟等凄婉词充斥其间,哀叹自己身世心境的“失路之悲”,和有感酬应送别的“亡国之思”,成了他的诗词的主基调。他的《初返居巢感怀》诗这样说:“失路人悲故国秋,飘零不敢吊巢由。书因入洛传黄耳,乌为伤心改白头。明月可怜销画角,花枝莫遣近高楼。台城一片歌钟起,散入南云万点愁。”
也许是自己也觉得心中有愧,所以他常有退隐之心。他和弟弟在老家近城处建别墅,取名“季鹰之园”和“司马之园”,“稻香楼”就是其中的代表性建筑。龚鼎孳曾多次携顾横波回肥,稻香楼成了文人名士聚会吟咏唱和的雅兴场所。龚鼎孳在清初文坛上地位很高,著有《定山堂集》47卷。他对家乡的贡献,一是关心家乡百姓疾苦,多次奏请朝廷减免地方百姓苦难,更主要的是关心家乡文化建设:重修中庙正楼,募修肥东店埠通济桥,重修庐州府等等,受到家乡人的赞赏。
还有一点为人称道的,是他利用自己的声名,尽可能地保护文人志士。清代著名词人陈维崧年轻时落魄潦倒,龚鼎孳慷慨相助,让陈维崧终生感念;他在刑部做官时,还为傅山、阎尔梅、陶汝鼎等明朝遗士开脱罪责,使他们免遭迫害……
纵览他一生的诗词,早年“桃花”时见,后期多见的是“柳”“兰”“梅”,对应在诗词风格上,早年以“艳宗”为风尚,继而“绮忏”,晚年“豪放”,似也能看出他的心境历程。
有比较可靠的考证,龚鼎孳墓葬是在巢湖市中庙街道的龚家山,即巢湖中庙白衣庵后。这个地方现在分属山下山梅村、小陈村和乱石谢,坟头已被削平,改为庄稼土地。不远处有一个叫龙脉村的,据说是龚家人请地理先生寻得的龙穴,其坟地内的碑石和石像生,或许仍在削平的土下。原有两百多年的古柏和松树,在抗战时被毁。果真在此的话,我想到了一个地方——烔炀镇岐阳村,这儿是巢湖市桃花节的所在。不“累”桃花城,在巢湖的对面选一处有桃花、梅花、松柏相伴的地方遥望家乡、守护家乡?
也许我想多了。但我想,在老城区发掘稻香楼、龚湾巷等文化内涵之后,把肥西桃花城、中庙龚家山也加进来,增添了两处人文历史景点之外,也让龚鼎孳这个人鲜活起来,何乐而不为呢?毕竟这是曾执清词坛牛耳多年、号称“江左三大家”之一的龚鼎孳!
“桃花城”现在已经是“城”了,但只是“工业城”,或许还可以加个“生态城”,而我更希望它还是个“文化城”!